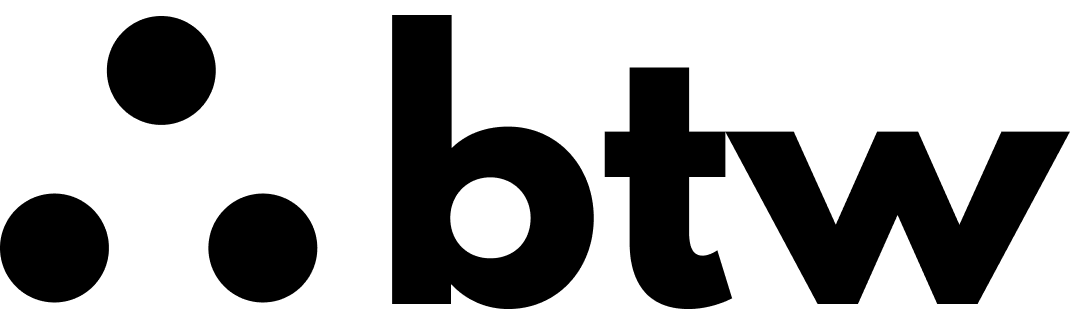#10
文化批评:网络、二次元的象征界、赛博大他者、资本主义与欲望的再生产
本文所提到的:
为什么二次元动画的视角不具有解放性?
二次元文化的危机:象征界的反噬,主体性的“归零”,符号的过剩,鲍德里亚式的“拟像世界”的彻底胜利
二次元文化作为维持社会规训以及欲望再生产过程而存在
顾名思义,所谓“二次元”的发明就决定了其与现实的对立关系,当然这并不是其之问题所在。齐泽克在做对于电子游戏的意识形态批判时明确表示了这样的担心:电子游戏让我们忘记了自我在真实界的存在,尤其是在911之后,人们仿佛觉得可以像cod中那样呼吸回血。虚拟让人们忘记了真实发生着的苦痛,这是“象征界的入侵”。当然这听起来确实很陈词滥调,但确实也很正确。二次元文化在阶级性问题上的态度是轻浮的,是所有文化形式中最为缺失的,在电影工业中,我们能看到鲁本奥斯特轮德的所提出的议题,在文学领域,绘画领域,音乐领域,更是数不胜数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二次元动画的视角并不具有解放性,而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和替代,这也是二次元文化的第一个危机所在。正如柏拉图所说:“孩子害怕黑暗,情有可原;人生真正的悲剧,是成人害怕光明。”
究其根本,我认为是由于二次元文化的高度娱乐性和社会再生产功能决定了其阶级视角的丧失,以一种福柯式的“知识-权利”关系作用在每个信徒之上。值得注意的是,二次元文化生产,重复了大量的符号,而符号的无限增殖也恰恰也意味着符号的无限缺失(符号的在场是意义的缺失,拉康语),这表征了全球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一种本雅明式的机械复制来推动经济共同体的,其背后是巨大的泡沫,是第三世界文明的消蚀,是工人阶级的不幸。由此可见,二次元文化不仅缺乏对现实的批判和改变,更加剧了现实的异化和虚无。
同时二次元准确地抓住了后现代身份政治危机的气质,作为止疼片让遭遇主体性危机的人们构筑起一个完全由其控制的象征的主体,这个过程是“主体性的归零”的过程,亦是欲望的再生产过程。在宏大叙事被消解之后,可以说二次元重建了信徒们的现实,但这个现实终究是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加西亚笔下的马孔多,爱伦坡笔下的厄舍府,不过是各种欲望和符号作为养料的无限再生产。
二次元文化是一种缺乏解放性、危机重重的文化形式,它既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的工具,它既是后现代的表现,也是后现代的陷阱,它既是人们的慰藉,也是人们的束缚。
齐泽克在《少于无》中这样说游戏王:在这个游戏中,卡牌是无尽的,新卡的加入都会伴随着规则的加入,所以从来没有一个能将所有卡牌容纳的总体规则,这便是拉康意义上的“并非全部的众多”。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谁在加入新的卡牌,而他们又为什么要加呢?面对一套可以无限增殖的象征秩序,我的态度已然明了了。